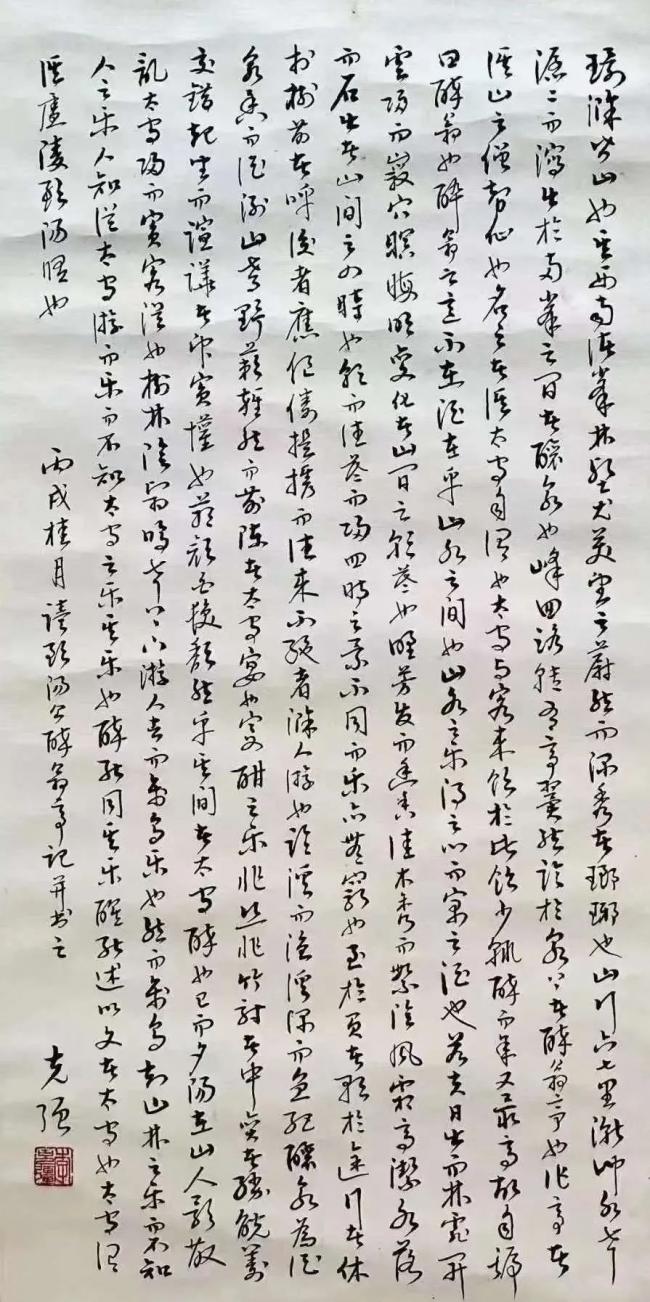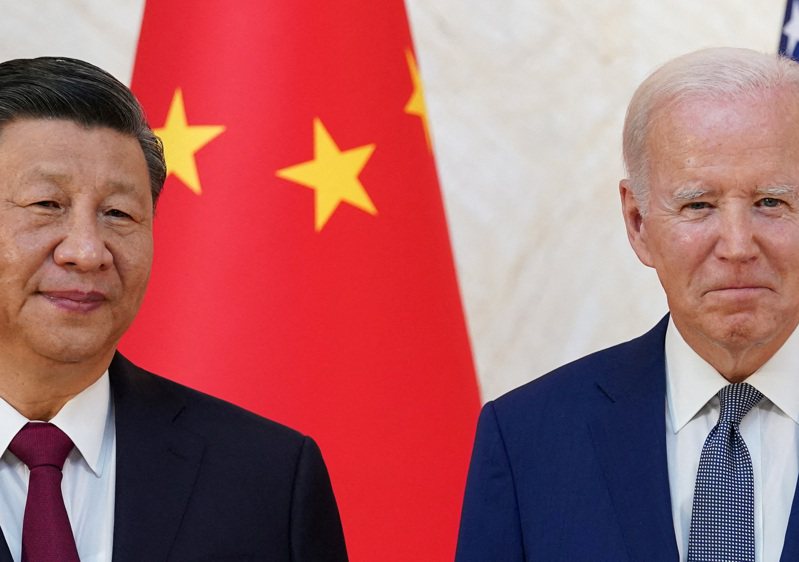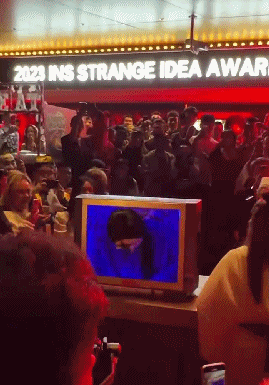"对狗的围剿,都是运动引发的人类互斗互害的延伸,是互害激发的黑暗激情,把人性最残忍的一面释放了出来"。
在中国,狗是相当苦命的。因而也就有“要你的狗命”一说;
狗命,即最贱的命。在中国文化里,狗基本是反派:狗腿子,走狗,狼心狗肺,狗汉奸,狗地主……“痛打落水狗“,人家已然落水,还要追着痛打,这要恨到何种田地?!打狗还不解恨,还要吃狗,广西有个狗肉节,年年挑衅世人的文明底线,公开提供人吃狗的直接罪证。
最近出了一只咬孩子的败类狗,立刻株连了它所有同类,又一次打狗高潮被掀起。我不由想起我亲历的历次对于狗的“严打”运动,似乎都发生在中国人心情恶劣,邪火攻心的时候。我童年的活玩具田园犬小黄,就是在四清运动末期被清除的,所以在我稚嫩的记忆里,“四清”就是“五清”,肃清狗类,是那场政治运动的收场曲。我少年时代的小伙伴小胖,是文革中期“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的祭品,(那场运动中,我家唯一一只下蛋母鸡麻花也做了陪葬)。
这种极致残忍,就是对自身不幸怨恨迁怒于其他更弱势力的生命,例如迁怒于一万年前就与人类相依为命的狗。那么我能不能这样推测,一周前这次剿狗运动,是人们在清零、开放、躺平,等等一系列不叫运动的集体行为引发的无奈,无力,由此对一切无解的失败感,叵测感,焦虑感,以及由一切负面感受生发的无名火、无名仇恨,终于找到了发泄物,因而一股脑向其发泄,而这承受人们发泄的,不幸又一次是人类最忠实的无言伴侣——狗。
倒霉的人,在发现还有比他更倒霉的生命,就会产生一丝幸运感,于是,制造这种终极倒霉蛋,是主动获得这一丝幸运感唯一手段,比如找出一个人,把他制造成某种“分子”,
这个倒霉蛋就诞生了,一瞬间,众拳齐下,那一众人,就自感是幸运儿了。这次被制造成倒霉蛋的,不幸又是陪同我们人类进化到二十一世纪的异类生命——狗。
二零零六年,我得到一只松狮犬壮壮。我父亲非常爱狗,所以我就把壮壮留在北京陪父亲。那时我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富起来了,心情普遍好转,不像四清、文革,人们一不留心,自己或家人或邻居就会被加以各种荒唐罪名挨打。正是对于挨打的恐慌和焦虑,使大家心情紧张阴郁,于是便把更无言更弱势的生命制造成倒霉蛋,向他们出手。这就是打狗的社会心理逻辑。我对富起来开心起来的同胞有信心,因为他们终于活到风调雨顺的年景,无气可出,无愤可泄,不用制造同类和异类的倒霉蛋用来出气,那么打狗终究成了大陆中国人的历史污点。可是在壮壮两岁时,却迎来了中国第X次打狗大运动。
我奇怪了,北京奥运召开进入倒计时,正是人们心情大好的年头,怎么又打起狗来了呢?难道狂欢也要以打狗来体现吗?当时传言,哪里又出了一两只不争气的狗,咬了人。对有着咬人潜质的狗狗们先下手为强,以预防它们咬伤奥运国际友人的后患。可是,较之败类之人,败类之狗的比例要小得多,总不见得因为人类有着杀人越货、人口贩卖、电信诈骗的潜质,就将人类赶尽杀绝吧?当时两岁的壮壮,毛发过浓,因此它看去体积庞大,想要在全民运动的亿万千里眼下逃生,难于上青天。
父亲拉下老脸,向打狗运动员们保证,他们下次再来,壮壮一定会被“处理”掉。我的老父亲买通了几个小区保安,打狗队一来,就通报他,他可以及时让家里的阿姨把壮壮从后门带出小区。有一次打狗队化整为零,潜入了小区才集结,父亲没有得到通报,壮壮在家里被堵了个正着,父亲又是一番发誓赌咒,一定说到做到“处理”壮壮,这次父亲被打狗队当孙子训,总算再次以老脸换得了壮壮的缓刑。
父亲再也不敢耽搁,当天让阿姨把壮壮送到她的老家——北京郊区的村落。等我决定把壮壮带到我们刚落脚的城市柏林时,壮壮已经消失,而再现我眼前的,是一条浑身无毛,(替代毛的是一片片渗出黄色液体的疮疥)形状大致像狗的生物。原来这位阿姨把它用铁链拴在前院,成了一只有声的看门活“石狮”。
两年的风雨霜雪、炎炎烈日,都落在它身上,一身好毛发,干了湿,湿了干,焐着沤着,整整两年,什么活物的毛经得起那样沤?再加上村里长疮长廯的狗,都可以贴身亲近它,它无论好恶,都得接受,因为它挣不开铁链。好在壮壮的中年晚年是幸福的,柏林的森林,湖泊,河流,还记得它肆意玩耍的笑靥。是的,狗是会笑的,假如你看懂狗们被追打时的痛苦和恐惧神色,你一定会看懂狗狗们有多少种笑容。
那个被咬的小女孩无疑是很不幸的。但她不幸成为这次打狗运动的主题(借口)。人们这两年内心积累的压力,一颗小火星就能点着他们无名火,简直是天然气爆炸的火势!种种个人的不顺心,对每一个非正常死亡的亲人亲友的哀痛,都往这狂暴火势上泼油。
我在台湾生活的三年里,一次坐我大表姐夫开的车,在一个红绿灯路口,他看见两条流浪狗闯过红灯,表姐夫牙缝里啐出一句:“妈的,所有动物里,人最烂!”接下来他向我解释:“这些人,脑筋一热养狗,不几天兴趣没了就扔出去,中国人最没理性,最不负责任!”
这句“不负责任”,大概是说到点子上了。假如每个养狗人都把狗当成家庭成员,为它们打预防针,管它温饱以及养老送终,街上的流浪狗就会减少已至消失,而且每一只狗都会健康,守纪律,即便有个别咬人的败类,也不会咬出狂犬病的重大后果。
当我们看到某处出了个败类狗,假如我们同时能想到汶川地震,那只救人的狗狗,想到电影“忠犬八公”等老了的身姿和脸容,想到在我们养过的或接触过的任何一只狗狗的眼睛,那些眼睛里除了死心塌地的忠诚,就是一眼见底的坦荡。假如我们能想到这些,我们举起的打狗棍还落得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