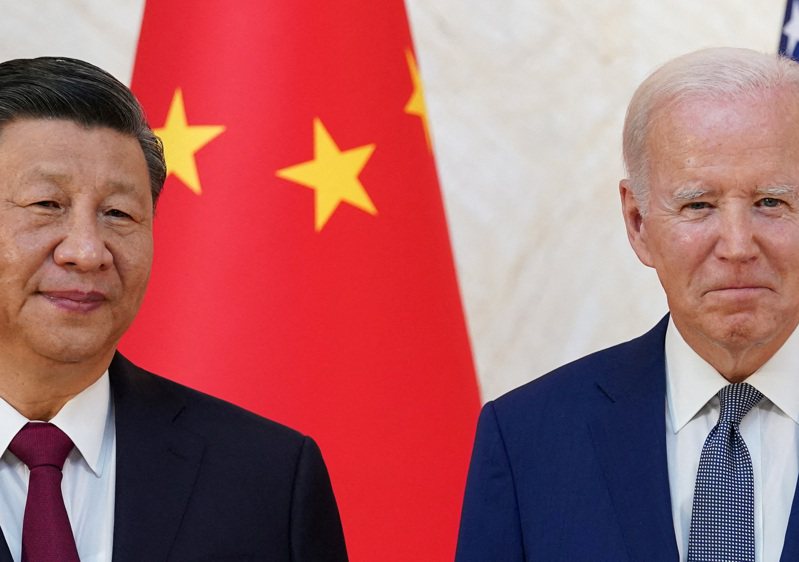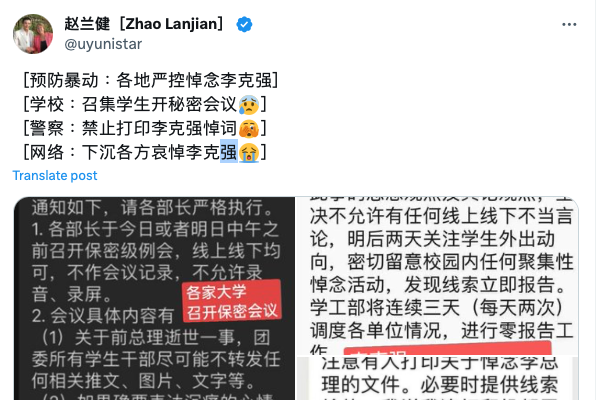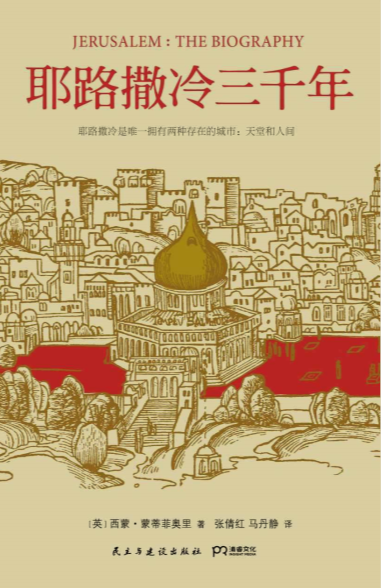
耶路撒冷的历史不仅是一部世界史,也是一部城市编年史,它讲述的是一座位於犹大山地长年陷於贫穷的地方城市。耶路撒冷曾被视为世界的中心,今日的它与过去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座城市是亚伯拉罕诸宗教争斗的焦点,是信徒日增的基督教、犹太教与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派的圣地,是文明冲突的战略要冲,是无神论与信仰龃龉的前线,是让世人魂牵梦系的去处,是惑人的阴谋与虚构的网络传说发生的地点,而身处於二十四小时轮播新闻的时代,耶路撒冷也成为全球镁光灯聚焦的舞台。在宗教、政治、媒体三方势力彼此拉抬下,今日的耶路撒冷比过去受到更密切的关注。
耶路撒冷是圣城,但也予人一种迷信、江湖术士与顽固盲从的印象;许多帝国渴望取得此城做为战利品,但实际上它不具战略价值;它是世界各大宗教的故乡,每个教派都认为这座城市只属於他们所有;它是一座拥有许多名字的城市——每个传统都顽固地认为只有自己的名称是对的。这座城市是如此柔弱,因此犹太神圣着作总是用阴性的词汇来形容它——它要不是诱人而充满活力的女子,就是美丽动人的女性,然而,耶路撒冷有时也被说成是无耻的娼妓,或被描绘成受爱人遗弃而遍体鳞伤的公主。耶路撒冷是一神的殿堂,是两个民族的首都,是三个宗教的圣地,而且是唯一拥有两种存在的城市——天国与人间:在人间就算得到无与伦比的恩宠,也比不上在天国的荣光。耶路撒冷既然能同时存在於天国与人间,就表示它能存在於任何地方:新耶路撒冷在世界各地出现,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耶路撒冷。 先知与先祖,亚伯拉罕、大卫、耶稣与穆罕默德据说都走过耶路撒冷的石板路。亚伯拉罕诸宗教诞生於此,世界也将於审判日在此终结。对信仰圣经的民族来说,耶路撒冷是神圣的城市,也是圣经的城市:从各方面来看,圣经既是耶路撒冷的编年史,也是耶路撒冷历史的读者,从犹太人与早期基督徒,中间历经穆斯林征服者与十字军,直到今日的美国福音派人士,他们为了符合圣经的预言,而不断更改耶路撒冷的历史。
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是十四世纪的历史学家,本书叙述的一些事件,他不仅是参与者,他的作品也是事件的史料来源。伊本·赫勒敦提到:“街头巷尾的民众是如此急切地追寻历史,他们渴望知道历史。国王与统治者也竞逐着历史。”这一点放在耶路撒冷是再真切不过。我们在撰写耶路撒冷的历史时,不能不认识到耶路撒冷也是世界史的主题、支点与脊梁。在网络神话力量无远弗届的今日,高科技的滑鼠与弯刀都是基本教义派可以选择的武器,因此我们现在对历史事实的追求要远比伊本·赫勒敦时代更来得迫切。
耶路撒冷的历史必须探讨神圣的本质。“圣城”一词充分表现出对耶路撒冷圣地的崇拜,但耶路撒冷成为神与人在人间进行沟通的核心地点,其中的意义到底是什麽?
我们也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世界上有这麽多地方,为什麽唯独选择耶路撒冷?这个地点不仅远离地中海沿岸商路,而且缺乏水源,夏季时烈日烤灼,冬季时寒风凛冽,这里的地形充满岩石、崎岖难行,显然不是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但耶路撒冷之所以成为兴建圣殿的地方,不仅出於人类自己的决定,其中也有着自然演进的因素:由於耶路撒冷从远古以来就有神圣之名,随着时代演进,它的神圣性也不断加添。神圣需要的不只是灵性与信仰,正当性与传统也不可或缺。激进的先知看到前所未见的异象,为了让大家明白他获得的启示,他必须解释过去数百年来的历史,使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并且诉诸地点的神圣——例如过去的先知也有过类似启示,以及这个地点自古以来一直广受崇拜。要让某个地点变得更加神圣,最有效的方法莫过於有别的宗教也想争夺此地做为他们的圣地。
许多抱持无神论的访客对於这类神圣说法感到厌恶,他们认为耶路撒冷到处弥漫着自以为是的盲从,整座城市似乎染上了迷信的疾病。然而抱持这种想法等於否定了人类对宗教的深刻需求,一旦我们无法了解这层需要,就不可能了解耶路撒冷。宗教必须解释令人类感到迷惑与畏惧的事物,例如快乐何以如此短暂,焦虑何以总是挥之不去:我们可以感受到有一股更强大的力量主宰我们的存在。我们敬畏死亡,而且渴望从死亡中找出意义。耶路撒冷是神与人交会的地方,也是末日时解决这些问题的地点——当末日来临,将会出现战争,基督与敌基督将会争斗,届时克尔白(Kaaba)将从麦加移往耶路撒冷,将会出现审判,死人将会复活,弥赛亚将会统治,天国也就是新耶路撒冷将会降临。亚伯拉罕三大宗教都相信末日,但细节因信仰教派不同而有所差异。世俗人士也许认为这些说法只是从古复述至今的陈腔滥调,然而别忘了,这些观念确实深植人心。在这个盛行着犹太教、基督教与穆斯林基本教义派的时代里,末日观念是一股令世界政治白热化的巨大动力。
死亡是我们永不分离的伴侣:自古以来,朝圣者前来耶路撒冷度过人生的最後阶段,死後就葬在圣殿山周围,他们希望藉此能在末日时复活,这种做法至今仍持续着。耶路撒冷不仅四周都是墓园,就连城市本身也坐落在墓地上:古代圣人遗留下来的部分骸骨,尽管已经乾瘪,却仍受到尊崇——抹大拉的马利亚已经乾枯发黑的右手,至今仍展示在圣墓教堂内希腊正教修道院院长的房间里。许多神龛,甚至於许多民宅就位在一堆坟墓当中。这座死者之城的阴森不仅来自於一种恋屍情结,也源自於与死者沟通的仪式:这里的死人宛如活人一般,他们只是在等待复活。耶路撒冷源远流长的争夺史——屠杀、破坏、战争、恐怖主义、围城与灾难——使这个地方成为战场,阿道斯·赫胥黎说这里是“各种宗教的屠宰场”,福楼拜说是“藏骸所”。梅尔维尔称耶路撒冷是被“亡者大军”团团包围的“头盖骨”;爱德华·萨依德则记得他的父亲讨厌耶路撒冷,因为这里“让他联想到死亡”。
这个连系着天国与人间的圣地,它的发展并不总是依照神的意旨进行。宗教的起源与深具领袖魅力的先知——摩西、耶稣、穆罕默德——息息相关。帝国的建立,城市的征服,仰赖的是军事领袖的活力与运气。从大卫王以降,个人的决定是耶路撒冷能成为耶路撒冷的主因。
当大卫在他的小王国首都建立简陋的堡垒时,人们显然无法预见这座不起眼的小城未来居然能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讽刺的是,尼布甲尼撒摧毁耶路撒冷反而使它成为神圣的典型,因为这场灾难使犹太人开始记录与赞扬锡安的荣耀。一般来说,这种剧变往往会使整个民族走上灭绝的道路。然而犹太人却依然生气蓬勃,他们坚定信仰自己的上帝,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圣经里记载了自己民族的历史,而这些纪录也为耶路撒冷的名声与神圣奠下基础。圣经取代犹太人的国家与圣殿,一如海因利希·海涅所言,它成为“犹太人随身携带的祖国,随身携带的耶路撒冷”。没有任何城市像耶路撒冷一样拥有自己的作品,也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如此左右一座城市的命运。
耶路撒冷的神圣,来自於犹太人以选民自居的优越主义。耶路撒冷成为被拣选的城市,巴勒斯坦成为被拣选的土地,而这种优越主义又由基督徒与穆斯林加以承袭与支持。耶路撒冷与以色列之地拥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这种观念不仅反映在宗教上越来越执着於让犹太人返回以色列,也表现在世俗上西方从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开始,到一九七○年代为止对锡安主义的热情追求。从那时起,巴勒斯坦人的悲剧叙事,连同耶路撒冷是他们失落的圣城,开始改变世人对以色列的看法。因此,西方的迷恋——把耶路撒冷当成属於全世界的城市——产生的影响好坏参半,它是一把双面刃。今日,这种情况反映在对耶路撒冷的严密监视上,也反映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上,其中的紧张与情感纠结远非世界上任何地区所能比拟。
然而,事情不像表面上看来那麽简单。耶路撒冷的历史通常呈现出一连串剧烈的改变与粗暴的反转,但我希望显示耶路撒冷其实是一座具有连续性与包容性的城市,它也是一座杂揉了各种建筑与民族的混合性城市,因此,我们无法以个别的宗教传说与日後出现的民族主义叙事来对其进行狭隘的分类。我尽可能透过家族的脉络来研究历史——大卫家族(Davidians)、马加比家族(Maccabees)与希律家族(Herodians),乌玛雅德家族(Umayyads)、鲍德温家族(house of Baldwin)与萨拉丁家族(house of Saladin),一直到侯赛尼家族(Husseinis)、哈立迪家族(Khalidis)、斯帕福德家族(Spaffords)、罗特稀德家族(Rot hschilds)与蒙提费欧里家族(Montefiores)——家族的历史可以显示有机的生命模式,而这种做法与传统历史的突发事件及宗派叙事格格不入。耶路撒冷不只有两个面向,它拥有许多彼此连结、交叠的文化,以及多层次的忠诚感——在这个多样且多变的万花筒里,你可以看见阿拉伯正教徒、阿拉伯穆斯林、塞法迪犹太人、阿什肯那吉犹太人、超正统派犹太人、世俗的犹太人、亚美尼亚正教徒、乔治亚人、塞尔维亚人、俄罗斯人、科普特人、新教徒、埃塞俄比亚人、拉丁人等等。每个人就像耶路撒冷成层堆积的石头与尘土一样,不断累积出好几种效忠的身分。
事实上,耶路撒冷的重要性起起伏伏,从未维持稳定,它总是不断变化,就像植物改变形状、大小乃至於颜色一样,而耶路撒冷也如同植物一般持续在相同的地点扎根。最近提到耶路撒冷时,人们总是说得天花乱坠,媒体把耶路撒冷是“三大宗教的圣城”挂在嘴边,二十四小时轮播新闻也以这座城市做为报道的焦点,但这都是相对晚近的事。其实,耶路撒冷有好几个世纪的时间完全失去了宗教与政治的重要性。很多时候是政治的必要性,而非神圣的天启再次刺激与鼓励了人们对耶路撒冷的宗教热忱。
每当耶路撒冷遭到遗忘,并且在历史上失去重要性时,远在异地的信众便开始致力於圣经事实的研究,无论他们身处麦加、莫斯科还是麻州,这些人总是将自己的信仰投射到耶路撒冷。城市如同一面镜子,可以反映出每座城市的居民心态,然而耶路撒冷却是一面双向镜,它不仅显示自身的内在生活,也映照着外在世界。无论是完全信仰的时代,还是建立符合公义的帝国的时代,抑或传福音宣扬天启的时代,以及世俗民族主义的时代,耶路撒冷都能充当每个时代的象徵,并且成为每个时代竞逐的目标。然而就像马戏团里的哈哈镜一样,镜子的倒影总是扭曲变形,模样怪异。
耶路撒冷令征服者与造访者沮丧与苦恼。真实的耶路撒冷与天国的耶路撒冷存在着太大的对比,使人感到失落,每年因此有上百人被送进耶路撒冷的疗养院。这些人罹患了耶路撒冷症候群,这是一种结合了渴望、失望与妄想的疯狂疾病。耶路撒冷症候群也与政治有关:耶路撒冷与合理而实际的政治策略格格不入,它生存在充满贪婪热情与冲动情感的领域里,理性在这里完全派不上用场。
就连赢得支配与真理也能提升耶路撒冷在其他人眼中的神圣性。拥有者越贪婪,竞争越激烈,越能激起本能的反应。预期外的结果定律在这里占了上风。
没有任何地方比耶路撒冷更能激起人们独占的欲望。然而这种占有欲却令人感到讽刺,因为耶路撒冷绝大多数的神龛,以及与这些神龛相关的故事,都是从别的宗教偷来或借来的。耶路撒冷的过去很多来自於想像。事实上,耶路撒冷的石头全来自不同信仰的神庙,与不同帝国兴建的凯旋门。绝大多数(也许不是全部)的征服会本能性地扫除其他信仰的污点,但同时间又强行接收了这些信仰的传统、故事与遗址。摧毁四处可见,但征服者更常做的却是不摧毁既有建筑,并重新加以使用与增益。圣殿山、大卫塔、大卫城、锡安山与圣墓教堂,这些重要遗址呈现的不是清楚分明的历史层理,而更像是反覆刮写的羊皮纸,或是丝线细密交织以至於难以分离的刺绣品。
不同信仰敬拜的圣物在人们的争相夺取下,使得某些圣坛接续与同时地被三大宗教奉为圣地;国王命令人们敬拜,而信徒也为此牺牲了生命——尽管如此,这些圣坛现在几乎已被遗忘:锡安山原是狂热的犹太教徒、穆斯林与基督徒尊崇的地点,如今此地几乎已无穆斯林或犹太教朝圣者,再度来此朝拜的主要是基督徒。
在耶路撒冷,事实的重要性比不上神话。“在耶路撒冷,不要问我历史『事实』,”着名的巴勒斯坦历史学家纳兹米·朱贝(Nazmi al-Jubeh)博士表示:“去除虚构的部分,耶路撒冷就一无所有。”历史对耶路撒冷的影响极为巨大,因此不断地遭受扭曲:考古学本身就是一股历史力量,有时考古学家拥有的力量就像士兵一样,他们受雇强徵过去,以为今人使用。一个以追求客观与科学为职志的学科,可以用来合理化宗教与种族的偏见,同时为帝国的野心提供正当化的理由。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与十九世纪传福音的帝国主义者都犯了这类罪行,明明是相同的事件,却在他们手中被赋予矛盾的意义与事实。因此耶路撒冷的历史必定是混合了真实与传说的历史。但事实确实存在,本书的目的就是说出事实,无论这些事实听起来有多麽刺耳。
我的目标是撰写一部最广义的耶路撒冷史,使一般读者都能阅读,无论他们是无神论者还是信仰者,基督徒、穆斯林还是犹太人。即使今日的耶路撒冷充满冲突倾轧,本书并不考虑政治方面的议题。我将依照年代顺序讲述耶路撒冷的故事,透过男男女女——士兵与先知,诗人与国王,农民与音乐家——的生活与创造耶路撒冷的家族来呈现这座城市的历史。我认为这是最能让耶路撒冷重现生机的方法,而我也将显示耶路撒冷复杂而出人意表的事实其实是历史形成的结果。唯有依照时间顺序加以叙述,我们才能避免以今人眼光评价古人。我试着避免以目的论诠释历史,以免给人一种印象,以为一切历史事件均不可避免。由於每个变化都是对前一个变化所做的回应,因此依照时间顺序叙述最能说明历史的演变,也最能回答这个问题——什麽是耶路撒冷?——同时也能显示人们为什麽做出某种行为。我希望这会是最有趣的讲述历史的方式。套句好莱坞的老词,我何德何能,能毁掉这篇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在数千部介绍耶路撒冷的作品中,只有极少数是叙事的历史作品。由於圣经、电影、小说与新闻的传布,四大时代——大卫、耶稣、十字军与以阿冲突——人们已相当熟悉,但其中仍有不少误解。至於四大时代以外的部分,我诚挚希望能让新的读者接触这些泰半已被遗忘的历史。
这是一部把耶路撒冷视为世界史中心的历史作品,但本书不想钜细靡遗地介绍耶路撒冷,也不想讲解每栋建筑物的每个壁龛、柱头与拱门。这不是一部有关正教徒,拉丁人或亚美尼亚人,伊斯兰法学的哈纳菲派(Hanafi)或夏菲派(Shafii),哈西德派犹太人(Hasidic Jews)或卡拉伊派犹太人(Karaite Jews)的琐细历史,也不是从特定观点出发的故事。从马木鲁克到托管时期这段穆斯林城市历史,我做了一些省略。耶路撒冷家族的历史已有具巴勒斯坦经验的学院人士进行研究,但通俗史家却很少触及这部分。这些家族历史至今仍极具重要性:有些关键史料尚未译成英文,於是我自己翻译了这些资料,并且访谈这些家族成员以了解他们的历史。但这些只能说是整幅马赛克作品的一小部分。本书不是犹太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历史,也不是上帝在耶路撒冷的性质研究:这些主题已有其他学者做过深入探 讨——最近的例子是凯伦·阿姆斯壮的大作《耶路撒冷:一座城市,三个信仰》(Jerusalem:One City,Three Faiths)。本书也不是以巴冲突历史的详细介绍:当前事件不是我想探讨的主题。然而,既然我要撰写的是一部涵盖所有时期的耶路撒冷史,因此我希望自己能做到一定比例的陈述。
我的任务是追求事实,不是裁决不同宗教间的神秘事迹孰是孰非。我当然没有权利判断三大宗教的神迹与神圣作品是否“真实”。凡是研究圣经或耶路撒冷的人都必须承认这里面存在各种层次的真实。其他宗教与时代的信仰总让我们感到陌生,而我们身处的时代与地点所通行的风俗习惯在我们眼里则总是合理。即使是二十一世纪,许多认为最符合世俗理由与常识的想法,其反映的社会通念与近似宗教的正统观点在我们的曾孙辈眼里也将荒谬得难以理解。宗教与奇迹对耶路撒冷历史的影响无庸置疑而且真实,我们必须对宗教怀抱敬意才可能了解耶路撒冷的历史。
耶路撒冷有几个世纪的历史鲜为人知且充满争议。只要一提到耶路撒冷,学界与考古学的辩论总是充满敌意,有时还出现火爆场面,甚至导致暴乱与斗殴。过去半个世纪的事件是如此具争议性,因此产生许多不同的诠释观点。
早期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与一些研究爱好者,将手边极其有限的资料加以挤压、塑造与粗暴对待,使其能合乎他们在充满自信下主张的各种可能理论。无论如何,我已经检视了一手史料与各种理论,而且得出了结论。如果我想保护自己免受各方指责,那麽这本书里最常见的词汇将是“也许”“或许”“可能”与“大概”。因此,我不会在每个可以使用这些词汇的地方穿插这些用语,但我希望读者了解,每个句子背後存在着数量庞大且观点不断变动的研究文献。本书每个章节都经过学界人士检查与阅读。我很幸运能得到目前最杰出的学者的帮助。
在这些争议中,最令人伤透脑筋的是大卫王,因为他的政治意涵太容易引起紧张,而且也与当代局势息息相关。即使采取了最科学的方法,这场论战的戏剧性与僵持远非其他地点或主题引发的争议所能比拟,唯一能与其相提并论的,大概只有基督或穆罕默德的性质。大卫故事的来源是圣经,他的历史生命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十九世纪,帝国主义结合基督教在圣地的利益,激励考古学家在大卫的耶路撒冷进行挖掘。这项调查原本带有基督教色彩,但在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国之後就转变了性质,由於大卫是犹太人耶路撒冷的建立者,因此为考古研究注入了宗教与政治的激情元素。由於西元前十世纪的证据相当稀少,因此修正派的以色列史家在估计大卫城的规模时做出比较保守的推测。有些人甚至怀疑大卫是否真有其人,这种质疑一方面令犹太传统主义者大为光火,另一方面也迎合了巴勒斯坦政治人物的心意,因为这使得犹太人的权利主张失去了正当性。然而一九九三年但丘石碑的出土证明大卫王确实存在。圣经在写作时虽然不是做为历史而存在,但它却能充当史料,成为我讲述故事的资料来源。本书讨论了大卫城的内容与圣经的可信度,至於现代针对大卫城引发的各种冲突,请参阅後记。
此外,在提到十九世纪时我们不可能忽略萨伊德《东方主义》的身影。萨伊德是出生於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基督徒,他後来担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文学教授,而且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世界最初的政治发声者,他认为“欧洲中心论的偏见隐微而持续地贬抑阿拉伯伊斯兰民族以及他们的文化”,特别是十九世纪的旅行者,例如夏多布里昂、梅尔维尔与马克吐温,他们贬损阿拉伯文化,而且合理化帝国主义。然而,萨伊德自己的作品却激励他的追随者将这些西方入侵者扫除出历史之外:这种做法相当荒谬。不过,这些旅行者确实对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生活一无所知或了解不多,而如同先前解释过的,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努力呈现当地居民真实的生活面貌。但本书不是一本论战作品,研究耶路撒冷的史家必须说明西方浪漫主义与帝国主义文化的支配对耶路撒冷造成的影响,因为这解释了中东为什麽与列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同样地,我描述了英国亲锡安主义的进展,无论是世俗的还是福音派的,从帕莫斯顿与夏夫茨贝里,到劳合·乔治、贝尔福(Balfour)、邱吉尔,以及他们的朋友魏茨曼。我的理由只有一个,因为这是对十九与二十世纪耶路撒冷与巴勒斯坦唯一最具决定性的影响来源。
本书的主要部分结束於一九六七年,因为六日战争本质上创造出今日的局势,足以做为决定性的区隔点。<後记>简略介绍到目前为止的政治发展,最後以详细描述三大圣地典型的早晨做结。但这个地区的情势仍持续变动之中。如果我要接续撰写直到今日耶路撒冷的历史,那麽这本书将找不到明确的终点,而且每小时就要更新一次。因此,我最後尝试说明的是耶路撒冷为什麽既是和平协议的核心,也是障碍。 这部作品综合了各种资料来源,我广泛阅读了一手史料,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我亲自与专家、教授、考古学家、家族与政治人物进行研讨,我曾造访耶路撒冷无数次,实际参观当地的圣坛与考古挖掘。我很幸运能发现一些崭新或很少被使用的史料。我的研究为我带来三项特别的乐趣:首先,我在耶路撒冷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其次,我阅读了许多作者的精采作品,从乌萨玛·宾·蒙奇德、伊本· 赫勒敦、艾维亚·切勒比与瓦希夫·贾瓦利叶,到泰尔的威廉、约瑟夫斯与阿拉伯的劳伦斯;最後,在可怕的政治危机中,我受到耶路撒冷人不分宗派——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与亚美尼亚人,穆斯林、犹太教徒与基督徒——的友善相待与协助,他们不仅信任我,也慷慨地提供援手。
我觉得自己整个人生都在准备写这本书。我从小就在耶路撒冷附近闲逛。由於家族的连结(在书里会提到这点),“耶路撒冷”一直是我们家的家训。无论我个人的连结是什麽,我都将描述实际发生的历史与人们信仰的事物。回到文章的开头,我提到有两个耶路撒冷,一个在人间,另一个在天国,这两个耶路撒冷都受到信仰与情感的统治,而非理性与事实。而耶路撒冷将一直是世界的中心。
我的写作方式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毕竟,这是耶路撒冷。但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总是想起劳合·乔治给耶路撒冷总督斯托尔斯的忠告,後者当时正受到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猛烈批评:“如果他们不停止抱怨,你这个总督就别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