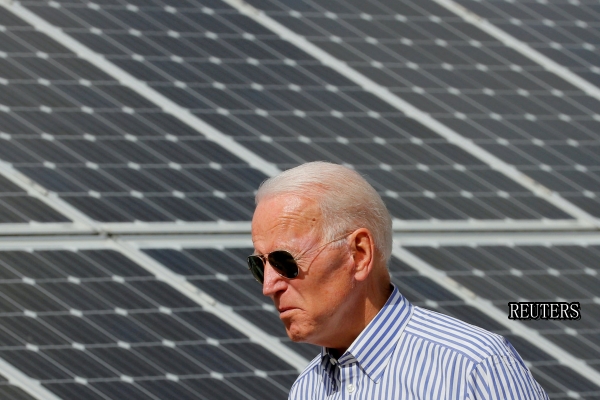2017年,住在缅因州乡下的杰弗里 · 霍尔(Jeffrey C. Hall)接到了一个电话,通知霍尔他与两位研究者一起分享了诺贝尔奖。接到电话,霍尔感到的不是开心,而是出乎意料。此时离他因为经费短缺被迫关闭实验室,已经过了十年。
十年前,被迫离开学术界的霍尔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表达了对学界的不满。在他看来,美国生物学研究已经陷入了体制性的腐败,大家都在围着经费转,科学明星掌握了大量经费,做出来的成果却并不是那么好。研究机构把PI获得经费看作理所当然,但却不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一旦研究进展不够快或者受阻,抑或是实验室的生产力优秀却没得到经费续约,那学术生涯也就离结束不远了。
自认不善运作的他,即使当时已经做出了日后获得诺奖的科学发现,也因为没法给实验室争取到经费而受到冷遇。“我承认,我对研究经费不足感到不满。我们实验室最近提出的申请都会被撕掉,而且往往伴随着风凉话和人身攻击[1]。”霍尔说。
没有经费,诺奖得主算什么
今年诺奖获得者卡塔琳·卡里科(Katalin Karikó)坎坷的科研和人生故事,在她得到诺奖后被反复讲述。不过,得不到经费支持的诺奖得主不止卡里科一个。
诺奖得主给人的印象总是荣誉等身,甚至进入了科学的圣殿,成为传说中的人物。在国内,很难想象一位科学家获得诺奖之后还为经费发愁。但诺奖得主的光环在激烈竞争的美国学界,并不能给科学家带来经费自由。
201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布莱恩·科比尔卡(Brian Kobilka)因为 G 蛋白偶联受体 (GPCR) 方面的研究获奖,获奖后他却表示“我现在还是为经费发愁,因为我的实验太昂贵了。去年9月以来我写了两个申请,现在正在写另外一个。”
当被问到研究中最艰难的时刻是什么,科比尔卡的回答是2003年和2007年两次失去资助。那是他度过了一段相当难熬的日子。他的妻子甚至需要在接受采访时澄清科比尔卡当年没有自掏腰包做实验。
霍华德-休斯研究所曾经在1990到2003年资助科比尔卡,但对他的进展不满意,停止了资助。“我知道他们对我的期望,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做我想做的事,尽管效果不太好。”4年后,他的另一个资助来源也发出警告,最后还是靠校方找来私人基金会支持才化解了危机[2]。
在科比尔卡看来,项目资助申请要求简直是个悖论。“只有高度创新的项目才能获得资助,但这类项目也有风险。你必须向他们提供能够成功的证据,但这样的项目很可能没有创新性。”面对这种学界22条军规,他能做的也只能是强打精神,一次次尝试。“这是一种挣扎,因为你必须获得资金并维持实验室的运转。在某种程度上,你必须相信自己。”
位于科学家荣誉顶峰的诺贝尔奖得主尚且如此,其他科学家争取经费的难度可想而知。“今天,当我申请资助时,因为我的工作我得到了无罪推定。遗憾的是,我不认为今天刚起步的研究人员会得到这样的待遇[3]。”科比尔卡说。
学术界习惯把工资的来源分为硬钱和软钱,硬钱是学校稳定提供的资金,意味着学校为科研买单。软钱则来自那些需要不断争取的项目,来源不稳定,而且学校从中隐身,完全没有支付教职员工的用人成本。如果一个教授的岗位是软钱资助的,一旦失去经费,就意味着会失去全部收入。
对美国生物医学界的调查发现。20 世纪 70 年代,高校会从自己的金库中为PI提供约75%的“硬”工资,到了21世纪,这个比例降低了很多。2014年,这个情况彻底逆转,一项调查了1050名PI的研究显示,现在他们的65%工资出自各类项目的资助。
这种转变源自资助大环境的变化,以及高校的贪婪和短视。单从生物医学学科来说,1970 年到 1999 年,NIH 预算每年增加9%。
在不缺资金的年代,美国高校也走了一回要大楼不要大师的弯路,把这笔钱投入了疯狂的实验室扩张中,实验室面积增加了6成。招聘来填补实验室空缺的科学家工资不再由校方提供,而是来自当时源源不断地NIH资助。
仅仅是那所拥有1050名PI的美国高校,2014年就因为NIH经费资助而节省了1.48 亿美元的薪水支出。此外,PI使用学校的设备还要被校方收取管理费,这笔管理费一般都是由项目资助方出,大概占到项目总经费的3成。通过这个手段,高校又赚到6000万。只靠扩张不靠科研,高校就从资助机构手里轻易拿到了大笔的钱,为此高校们更疯狂地贷款建实验室扩张[4]。
泡沫终归有破裂的一天。2005年后,NIH资助增长陷入停滞。考虑到通货膨胀,2017年的经费比2003年要下降接近20%。NIH项目申请的成功率曾经常年稳定在30%左右,但2006年后暴跌至15%[5]。
但此时,科研的风险已经从校方转移给了科学家,泡沫破灭后,依赖项目资助提供工资的PI们生存变得艰难。扩张实验室带来的管理费用暴涨,更是进一步减少了项目资助的意愿。
高校对教职员工的评价标准变得围着经费转,只看资助机构的“自然选择”,拿到资助才能获得终身教职。即使生产力足够好,发文比同事都多,如果拉不来资金只能用学校的钱,那也只能被学校看作负资产,被评价为科研不活跃从而失去评选终身教职的机会。
资助机构不仅钱少了,眼光也日趋保守。对33篇发表于1958 年至1998年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论文资助来源的调查显示,这些论文接近一半都有NIH的资助,NIH对这类论文的资助比率是普通论文的2到6倍。可以说,当时NIH的资助是美国学术创新的支撑者之一[6]。
但如今的NIH更喜欢资助那些成熟,风险小的想法。对2010年至2016年资助内容的研究发现,NIH更爱资助那些基于学界7到10年想法的研究,不愿意资助那些基于最新想法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区别,基于新想法和成熟想法的研究都有相同的资助比例[7]。
资助更多集中在了年龄更大的PI手中。从1980年到2008年,首次获得NIH资助的生物或医学研究人员平均年龄从36岁增长到42岁。可统计数据显示,诺贝尔奖生物医学奖或者化学奖得主中,进行开创性研究的平均年龄只有41岁。
也就是说,过去诺奖得主可能是在36岁获得第一份NIH资助,经过几年的努力进入原创的爆发期。而今天越来越卷的资助竞争,没有为潜在的诺奖得主们留下多少潜心搞研究的时间[8]。
2000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得主埃里克·R·坎德尔 (Eric R. Kandel)曾在接受诺奖采访时表示,很幸运赶上了一个资金充裕、鼓励新想法的时代。在那个年代,年轻人只要有任何业绩记录,就很容易获得科学资助。而现在竞争者多了,政府和资助机构,包括霍华德-休斯(HHMI)研究所都变得保守。如果在现在这个年代,他觉得自己没法得到资助[9]。
滑落的教职员工
一次经费申请失败,可能就会摧毁一位潜在诺奖得主的学术生涯。
2008年的诺奖颁奖典礼上有一位特殊的嘉宾,面包车司机道格拉斯?普瑞舍(Douglas Prasher)。他不是谁的亲友,但当年三位化学奖得主都在发言时对他表示感谢,因为如果历史稍有改变,现在可能就是这位面包车司机站在诺奖的领奖台上。
普瑞舍当年是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PI,领导着绿色荧光蛋白(GFP)的研究工作。在这个领域里他是先行者,两位诺奖得主马丁查菲和钱永健,当年都是从他那里得到第一批GFP样本。
可惜普瑞舍的想法没有得到资助者的支持,他当年的申请被NIH否定,只能依靠手头一笔美国癌症协会的资金来支持研究,这笔资金根本没法支撑到他实现自己的设想。
资金缺乏带来的研究不顺,让普瑞舍失去了信心。他本来已经准备进入终身教职评定的流程,但他也自知研究不顺的自己难以通过,于是他停止了评定流程,转去寻找其他职位。走之前他把GFP基因样本寄给马丁?查菲和钱永健,普瑞舍觉得这是他能做出的最好选择了,“他们都在资金雄厚的机构,而我却在为获得资金而苦苦挣扎。我没有研究生,没有博士后。”
离职之后,普瑞舍像坐滑梯一样跌落。他去了美国农业部工作,先是在科德角,后来在马里兰州的贝尔茨维尔开发识别害虫和其他昆虫的方法。这时连受打击的普瑞舍心态已经很糟,他和上级相处的不好并且陷入抑郁,搬去马里兰州也给在上学的孩子带来很多麻烦。
他的下一站是亨茨维尔,在那里他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一个分包商工作。这次他对工作的感觉不错,但很快这份工作也没了资助。一再搬迁的他考虑家庭不再搬走了,可在这个地方也没有其他的科研机会,他最终选择做一名司机[10]。
诺奖颁奖礼之后,普瑞舍曾经想要重归学术界。但即使有多位诺贝尔奖得主背书,本身曾经也是名校的PI,普瑞舍还是很难找到一份科研工作。最后还是一直宣传普瑞舍贡献的钱永健,为他提供了一个钱永健实验室的机会。
努力、天赋、兴趣,普瑞舍不缺乏任何一点,他离诺奖的距离不过是一份足够的资助。这一份资助的差距,就足以让他从终身教职序列的教授,跌落到时薪8.5美元的司机。
从高处滑落和从来没有获得过机会,很难说哪种经历更糟。
今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获得者之一的卡里科,从未获得过终身教职。不仅如此,她根本不在终身教职的序列中,属于非终身教职序列(Non- Tenure Track)教职员工,甚至没有参与非升既走竞争的机会。
在美国,非终身制教职正在迅速取代传统的终身制教职,成为高校教师队伍的主流。根据美国教育部数据,目前全美高校教师中71%为非终身制教职员工,其中兼职教职员工占51%,全职员工占20%。零工经济早已占领了高等教育行业。
70年代,终身教职的比例还能占到40%左右。但90年代以来,随着大学的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本科生入学人数从 1995 年的 1220 万人增加到 2011 年的峰值 1810 万人。大学需要额外雇用数十万名教职人员。
高校本可以保持终身教职与非终身教职的比例大致相同,利用新的学费收入来创造更多的终身教职职位。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临时教职人员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多,达到 110 万人。相比之下,终身教授和终身教授的数量仅增加了 9.6%,达到 436,000 人。学费没有用在提高教师待遇上,只是养肥了校方[11]。
终身还是非终身,全职还是兼职,为高校中的教职员工划出了分明的等级,各个等级之间是难以逾越的高墙。终身教职序列的员工是校方认可的潜力股,多少会得到校方的支持。而那些非终身教职序列的员工大多只能靠申请到的经费来勉强维持自己的研究,一旦没有经费就面临着走人的风险,很难长期投入一个科学项目。
最底层的是兼职教师,他们过着的是这样的生活:下课后学生回到宿舍,老师则是回到自己的车里,匆匆吃上一个芝士汉堡,然后开车去另一个城市上一门完全不同的课。如果考虑课前的准备和课后批改作业的时间,他们的时薪勉强够到最低工资标准。
在薪酬方面,全职非终身制教员的平均工资仍比终身制教员低10%,兼职教员的平均工资则低60%。学校也缺乏清晰的非终身制教员加薪政策,导致他们的收入增长不稳定。另外,移民、少数族裔和女性占非终身制教员的比例,相比终身制教员明显偏多。
就业稳定性方面,64%的全职非终身制教员都只有一年的短合同,大环境一旦变化,先遭到解雇的往往是非终身教员。非终身制教员还经常承担超出教学任务的学术工作,比如课程改编、学生支持等工作,但拿不到相应的补助[12]。
卡里科的情况好一点,至少合同时间比较长。但她也受足了刁难和歧视,她在自传里提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很多学生都对我翻白眼——对我那些似乎与他们职业理想并不直接相关的文章,对我在实验室里对精确度的要求,对我是一名非终身教职的教师这个事实[13]。”
新冠疫情成就了卡里科,mRNA技术在疫情期间一战成名。但在疫情的三年里,更多和她境遇相似的科学家失去了机会。疫情期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一份报告发现,20%的受访机构终止或没有续聘全职非终身教职教师,很难知道其中到底有多少被埋没的“卡里科”。
卷不动的年轻人
从诺奖得主到功成名就的PI,再到挣扎在繁重工作中的兼职教职员工,没有人能逃过学术界无处不在的竞争。不用说做原创的、有风险的研究,仅仅是维持自己的地位和生存都要耗尽心思。但其中承受压力最多的,还是最底层、最没有权力的年轻人。
“在我那个年代,博士后论文为零也能获得教职,就像我的情况一样;但现在,成功应聘者的简历看起来就像旧时代新晋正教授的简历。”这是诺奖得主霍尔2008年对学术招聘市场的评价,到了现在,学术职位竞争的激烈程度只会更夸张。
一项研究显示,在2013年申请“初级研究员”岗位的演化生物学家,比2005年申请同一岗位的科学家发表量几乎多了一倍。同一项研究还发现,科学家从首次发表到被聘正式为教职的时间,也从平均3年左右增加到了8年左右[14]。
在美国的大学招生论坛collegeconfidential上。一位家长分享了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位麻省理工本科,2013年哈佛博士毕业的研究人员,曾经在Science 和 Cell 上都发表过文章。但她毕业后做过两次博士后,担任过三个不同的兼职教授,直到四年后才找到一个正式的教职[15]。
这仅仅是为了争取一个不稳定的、到期可能不会续聘的教职,至于终身教职序列的职位就更是可望不可及。
年轻人还赶上了最不愿意退休的一波老教授。因为1994年美国取消了终身教职教授70岁强制退休的规定,导致越来越多的老教授占着职位不放。从1995年到2010年,教师队伍的平均年龄高了两年半,据估计,如果大学退休年龄没有发生变化,招聘率将会增加约 20%[16]。
一项研究把人口模型用在了学术界就业上,发现2011年的学术就业市场的R0值达到了7.8,也就是说,一个终身教职序列教授平均会带出7.8个学生,但只会空出一个职位,平均下来只有12.3%的学生能得到学术职位。具体到STEM领域,只有 17% 的STEM专业博士在毕业后 3 年内找到了终身教职序列的岗位[17]。
过强的竞争,带来了明显的分层。2010到2020年,得到终身教职序列职位的研究人员出身的学校高度集中。从总体上看,前20%的高校输送的学生,占据了80%的终身教职序列职位。
其中最有名的五所学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和斯坦福大学,占据了差不多八分之一的职位。而且出身弱势学校的博士,大部分都流向了更弱势的学校,能逆势去名校教书的比例很低[18]。
大部分年轻的科学家职业生涯要从博士后开始。博士后通常是通过教授获得的科研基金聘用的,因此他们只负责一件事:创造有价值的成果。对博士后来说,发表等于资助等于就业。于是一群30到40岁之间拖家带口,拿着平均不到4万美元的年薪,把科研最宝贵的时间用在完成导师的项目上,成为实验室里的工蜂[19]。
有部分PI对这样辛苦的博士后还不满意,他们选择从外国招聘廉价博士后,利用签证续签逼他们接受苛刻的工作环境。“他给我们承诺工资的百分之一”“外国博士后睡在实验室的地板上,每周工作 100 多个小时。”相比科学家,可能用奴隶贩子来称呼这些实验室老板更为恰当[20]。
卷够了的年轻人,正在大批的逃离学术界。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美国获得生命科学博士学位的毕业生,获得与学术界工作的比例都占40%到50%,去业界工作的的只有20%到30%。但到了2019年,两者所占的比例对调,去业界的比例占到40%以上。
生物医学专业的博士毕业生进入产业界后,起薪中位数预计在 10.5 万美元。与此相比,博士后的起薪中位数只有 5.3 万美元。而且生物医学行业还在蓬勃发展,2012 年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的年度风险投资金额约为 50 亿美元,而到了 2021 年这一数量增长到了 380 亿美元。与之相比,学术界只剩理想这一块遮羞布了。
博士毕业生是支撑学术就业市场的基础,大批博士生转向业界,很多实验室立刻感到了招聘博士生的困难。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建立实验室萨拉·扎卡拉(Sara Zaccara)就发现,她一个合适的博士后也招不到,实际上连她自己的博士同学也都进入了产业界,进入学术界的她反而像一个异类[21]。
或许离开是更好的选择,卡里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受到多年冷遇后,去了德国BioNTech公司工作,后来在新冠疫情期间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在那里没有拒绝资助她的官方机构,没有对她翻白眼的学生,没有拿绿卡谈条件的行政部门,有的只是自己的研究。这样的环境,可能才是学术界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