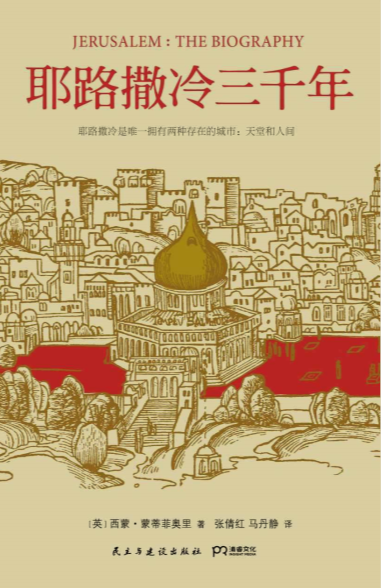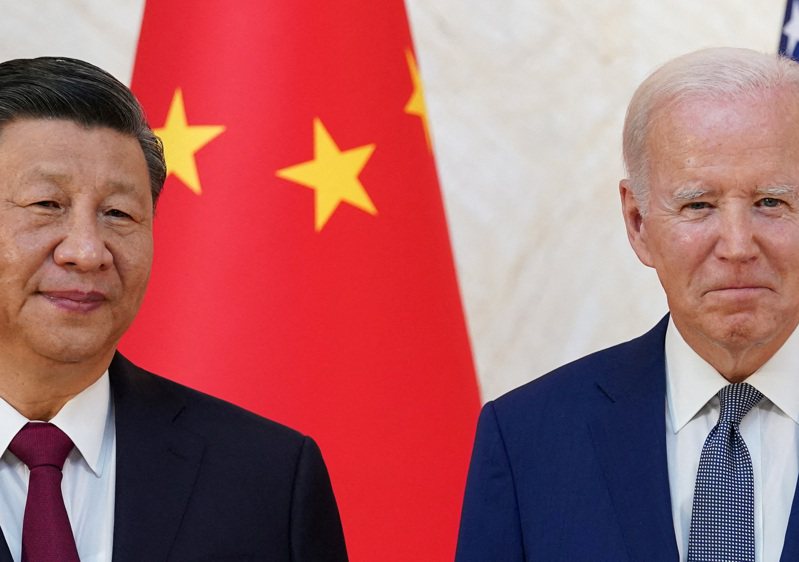我的少年到青年,是过渡的十年,没所谓的个人藏书,只记得一座少年儿童图书馆,上海复兴中路独立洋房,长甬道,两边金色梧桐,对面是常常传来琴音的法式公寓“陕南邨”(旧名凡尔登花园)。没读完初一,风景被“文革”画面切换,暑假后,全市学校继续停课“闹革命”,我父亲是打倒对象,九月,全家被迫搬到沪郊,因此很少回校,只一次听同学议论,复兴路少儿图书馆的大门,早被钉死了。这话意思是,此图书馆向来是少年人注意的目标。我大哥学校的多个学生组织,也紧盯校图书馆。革命前同学们进馆,有规有矩,文雅借书,清楚书目详情;等逢乱世,面临一种人人可以“抢”的市面,部分少年人的盘算惦记,就在如何伺机采取“革命行动”。果然有一天,某少年急急来报——就在前夜,校外某一学生组织突然“砸烂”了本校图书馆——其实是悄无声息的“转移”更准确,深夜隐秘大动作,在驻校多个革命学生组织的眼皮子底下,搬走了所有“有批判价值”“反动”图书,不声不响,顷刻间不明去向。忽遇变局,所谓“措置太骤”,肯定有了内鬼!引发了学生领袖们相互攻讦,私下都极其懊恼,有人形容说,这就是“噬脐之悔”。
那是鄙视图书的时代,也是极为珍视书籍的岁月,所有公私图书之劫难,学生肯定是主要执行者,但因避讳与遗忘,鲜见这方面详细回忆;1966年的书基本有两种命运,一是“封存之书”,运至仓库或地下防空洞,沉入无尽的黑暗,蒙尘或腐烂;另一批是活泼的“流通之书”,经由革命学生的抢夺,传递,水银泻地,静静回流于社会各暗处,记录后者这一类的温和文句,可以有(包括本文)……例如:他或者她,如何因一个偶然,受了某一本或半本零缣断素之影响,改变了什么观念,打开了人生另一个什么名目的窗……这类谰语浮言慢慢汇合,形成这一辈青年的“地下”阅读史。
1969年,我已随大批同龄青年,去到黑龙江黑河地区农场务农。全场聚集各城市青年五千余,附近另有同等规模“格球山”“七星泡”等大型农场,招募各城市青年无数——其时中苏关系异常紧张,农场原大批劳改人员全部迁走了,也就以大量的城市青年回填,接受原劳改干部的领导,某个分场的青年们,甚至直接入住到四面高墙、岗楼电网的原劳改犯营舍。短期内,有些农场给青年们发长枪(子弹只一枚),朝鲜战争的老枪,包括二战期间伤痕累累的马枪。十月初开始上冻,不久就下雪了,传闻某一青年在雪后的深夜,跨过了冰封的黑龙江,投奔去到对岸,原因不明,雪地留下他一串孤独的脚印,对于这类“叛逃”,苏方往往不予接纳,最后通知了中方边境,送回一具蜷缩冻硬的尸体,死者书包内,发现了一中文版《驿站长》,一本《外国民歌两百首》(当时被禁最著名“黄色歌本”),解剖发现,他的胃是干瘪的,只剩一些土豆残留物。之后无数个寒冷的夜晚,农场田野上空出现幽灵一般的信号弹,大批青年被哨子惊醒,摸黑慌忙穿衣集合,在雪地里急行军,四处探查。当时我知道连队某青年,同样秘藏了一册《外国民歌两百首》,每次半夜起身,他都把这个本子塞在胸口,这位歌唱爱好者向我解释,这是他最珍视的东西,就是今夜他忽然死了,暴露了怀中之物,也在所不惜,“我至少出名了”。黑暗中,他的牙齿发出亮光。
黑龙江两岸,当年处于极端的抗衡之下,所谓苏俄小说,仍旧是此岸青年的“地下阅读”主干,放眼是广阔的雪原,白桦树,马拉雪橇,春风里手风琴的琶音,山楂树满树繁花,都让青年们联想译文中的风景。在黑暗中夜行军之时,眼前总在闪耀《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的火光,听闻肖洛霍夫《顿河故事》铿锵的中译语言,这奇怪的通感,应为中苏蜜月期间那挥之不去的,天量印刷数字所形成的印象碎片,与那种反复诵读,强化于大脑的烙印有根深蒂固的必然关联。
这代青年直到如今的老境,被硬性定义为所谓“青春无悔”,其实却百孔千疮,爬满了虱子,如何存有整齐划一的境界内涵?即使是来自各家庭、各人、各地区差异,就是盘根错节,无休止的恩怨情仇,永在生存争斗的浑浊状焦虑中,当年他们统一的习性是——除却了只念“红宝书”之积极小干部,都是一致积极传阅“旧书禁书”,读本五花八门,大量出自上海,这应是凭借了当年他们更年轻双手的剥夺与传达,使这一类阅读活动多么活跃而隐秘,以至后期呈现了半公开的种种生物链,几乎每时每刻,连队都有陌生“新品”露面,口碑最佳,最合适男女心理,最注目也最文艺普及的,始终是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或冻毙者书包里的忧伤《驿站长》,沙俄军官,龙骑兵,客厅沙龙,缱绻男女之恋,“达吉娅娜”爱之忧伤,“冰花在爆裂,田野闪耀着银白色的光”,甚至普希金陌生的经验与格言,“我们爱女人的心越淡漠,就越能博得女人的爱……”是坚冰背景之下的青年们,更需要心灵的柔化吗?待等我们走到黄昏的田野,听到白杨高处的风声,心头也自会流淌屠格涅夫《待焚的诗篇》:
到那地方,到那地方,
到那辽阔的原野上
那里的土地黑沉沉的像天鹅绒一样
那里的黑麦到处在望
静静地泛着柔软的波浪
那是个好地方……
这大概就是当年该国文本能给予我们的,唯一的肯定与安详。
至于被老一辈读者目为好书,更苏联式的叙事,盖有私人或者上海某某图书馆圆章的《三个穿灰大衣的人》《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士敏土》等等,以后的几年里少人光顾,可公然摊在床铺上,是吾辈觉得枯燥,还是艰深呢?在这缓慢时光中,在这奇异的读书之境里,我眼前会出现一个传送带景象,大量的苏俄译本在眼前缓慢蠕动,清晰和模糊:《白夜》《州委书记》《叶尔绍夫兄弟》《多雪的冬天》,包括少见的瞿秋白《赤都心史》《饿乡纪程》,高级水彩纸印造的苏联大部头美术画册,苏方专家的《建筑钢笔画教程》……记得有一天,云雀在高空鸣啭,我在回场的马车上颠簸,发现车夫身边装草料的麻袋里,缓慢滑出了一本《铁木尔和他的伙伴们》,翻开扉页,一个熟悉的蓝色图章憬然在目:“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
苏俄小说的阅读节点,始于1980年代出版《日瓦戈医生》、三卷本《古拉格群岛》引起的颠覆,逐渐逐渐,也都被缓慢化解了,人们开始关注和收藏“垮掉的一代”、法国新小说、莫拉维亚、南美作家系列等等等等。稍后,我朋友供职北京的“苏联文学研究所”永远关了门,再以后的以后,却在王朔电影里,见一群“文革”青年穿父辈的苏联式“将校呢”制服,大唱苏联歌曲的镜头,与我的经验搅拌一处,涌起恍如隔世的恶心感。再过若干年,“垮掉的一代”、法国新小说、莫拉维亚、南美作家系列等等等等著作,已在很多书架上泛黄,面对译本,我不再喜悦雀跃的情景之下,是2000年后出版界发掘的巴别尔《红色骑兵军》《哥萨克的末日》,翻开那些文字,苏俄式样的末日气息,仍然毫无阻拦,登堂入室,使人心率加快,让我想到了我的青年,想到遥远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顿河故事》的审美与口吻……
这个邻近国家对我的阅读影响,实在难以言说。
作者附识
写完此文,即发给遥在他国的胡承伟先生看,他是当年老大学生,回复如下:
老兄的文章,不论长短,都是对书的崇敬。
提到书,我的年代与你不同,也有不少入骨的记忆。
北大在当时没有烧书行动,再说普通学生也没有多少好书。记得1968年3月,武斗中聂元梓派攻占了我住的学生楼,当时我不在宿舍。占楼者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到每一间搜索,声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事后检查,箱子里全国粮票和几十元人民币不见了,更令我痛心的是,俄语系一个朋友借我的《金批三国》不翼而飞。去年见到这个朋友,还是说不尽的对他不起。
几年后,我被分到河北的一个县城,在城关镇教书。很快就和县图书馆搞好了关系,每天值班的只是一个军官太太,此女似乎对我有好感。一天突然打开里面的仓库,让我进里面。好多年都没有这样的兴奋,连王力的《古代汉语》和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都叫我眼前一热。当然,上面有规矩,不能往外借出这些书,我不想破了规矩。以后的几年,只要没人,她就愿意站在仓库门口和我聊天,而我则在里面找书。再后来,她的夫君部队调动,她也离开。至今我还自疚当时利用人家的感情,只是图得一些阅读。
细捋回眸,诸多图书记忆,历历在目。